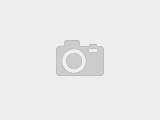|
經過那個男人發狂剁床的事情以后,也是自老白八年來第二次覺得對面可能會發生什么詭秘大事開端。在很久以前,他就見過對面發生過一次大事。那年還是深冬入夜,老白習慣地朝著老地方望去,發現一個老頭在對面樓道間搖搖晃晃。 究竟發生了什么呢?那細微的搖晃猶如鐘擺,往細了看,脖子上還有……掛有繩子?! 上吊了! 當時老白還因為那事兒做了很久的噩夢,那次的事情惹的很大,很多人都因這事兒受到上門的調查,到了最后,是后來發現是一場剛出獄后的抑郁癥自殺。因為迅速結案,后來便不了了之了。 那次事件給了老白某種刺激——在暗地里觀察到人命關天的事情,這似乎是他那爛泥一樣的生活中最最缺失的新的激動。而這次,他很快就察覺到,他所見到的事情似乎和那次事情有某種相似的味道,究竟是什么味道平常生活中很難說清,因為那是一種類似于刑偵者的直覺。
但要說邋里邋遢的老白是刑偵者?光是想想就帶著些諷刺的意味。 雖然說一開始見到剁床當時確實是有些害怕——其實說是害怕,不如說更像是一種震驚,因為對于人而言害怕會持久,但震驚卻不會。而后很快,老白也能對當時發現的事情不抱著更多態度。而且兩個人之間本來隔著一條街,對于住在20幾樓高度的他來說,這條小街就很能代表自己的安全。 他明白,只要不過去,那個男人愛怎么怎么都和自己無關。只要不逾越界限,就能一直保持著自己那個上帝身份不變。 但是不久以后,事情卻出現了老白意料之外的發展。 原先自己一直都找不到的女人卻在有一天出現在了他家里面! 應該是第一次邀請吧。他望著那邊想著,這時候是在白天。近些天來,老白猶如某些職業記者一般,竟然對那樣的事情發展有所好奇,似乎是對某種人命關天的發展有所好奇,于是,甚至白天有時候也會偶爾拿出望遠鏡朝著那邊望去。 然而看到對面竟然出現了一個女人不由得奇怪起來。 “看口型,是普通的聊天吧。”老白向自己說道。 但是一個女人進入一個男人的家里面在老白內心還是有種抵觸。 并且那個女人也是他一直以來魂牽夢縈著的部分。 “但是為什么會出現在那里?” 老白不甘地想著一切可能,思緒飛馳于各種讀過的偵探小說、愛情故事。 那個男人本來看上去就挺不錯,身材好。外觀更是貼切,在一身的肌肉搭配下,襯衫的輪廓也能擁有極其勻稱的美感。那屋子里裝潢也好,也能隨便扔掉奢侈品一樣的餐具,看上去月薪也不差。而老白呢?一身邋遢,胡子已經好幾天沒剃,頭發更是糟亂。身材不好,遠遠望去仿佛一身的皮肉是有人故意胡亂掛在骨架上面。 即便是女人有意在兩者之間做出選擇,明理人一眼就能看出答案。 其實老白根本就沒有一丁點機會,光是十年的家里蹲這一點就足夠讓人絕望。 但是究竟自己又能有怎么樣的說話資格呢?自己究竟和那個男人之間又有什么樣的區別呢?他似乎在潛意識中就已經和那人進行對比。但是卻沒實際想出來,因為誰都明白,老白的自己的長處竟是一個也沒有想到。反倒是對方小毛病系數了個遍,“愛照鏡子秀肌肉肯定是自戀,怕蟲,肯定也能娘……”如此這般。 唯有一個壞處,讓他堅定了最后自己主動干涉的理由。 “危險。”最后他想到唯一的一個也是最合適的理由驅動自己。 腦中不斷重復著這樣的詞匯:“危險!危險!危險!……” 那個男人十分危險。 唯有他一人知道。
8 受到某種樸實的絕望影響,是在人最最平淡中將要發覺自己正漸漸老去卻一事無成的時候,會突然性地抓住某種可能性不放。 比如,對什么東西的渴望。 但是我們都知道,所有渴望都有源頭,卻很少有人能夠對這源頭知根知底。那么究竟用怎樣的核心要素才能支撐起一個渴望的巨大銅像呢?答案往往出乎意料—— 最簡單的,也會是最有效的。 其實相比于突兀的事件沖擊,一股持久的“不甘心”在常年累月的積累后,更能發揮出巨大的作用。而且,渴望被實現可能性也會因之而被放大更多。比如說,有人會想“如果我能救她,至少能證明我還沒差到那種地步。”換個角度而言,即便一個人過慣流水般糜爛的生活,正因為背水一戰,所以也能因為身負渴望,重新開始正視自己。 于是,自從第一次夢見那個女人以來,渴望的種子已然在老白心里生根發芽,并在最可能失去那個女人的時候,行動便就隨之而來了。 “我要救她。” 那個女人似乎在后來的時間內也變得偶爾也會去那男人屋子里去玩,雖然那時候并不會一對一,因為也會帶一些朋友過來,有時候也會玩得稍晚。所以,若是在晚上的話,趁著女人要回家的時候,老白也能在黑夜的保護色中,順利跟蹤下去。畢竟,白天的話,小區里的熟人的確是太多了。 當然,也是在老白跟蹤的途中,還有好幾次差點被發現。 但是在他略顯拙劣的演繹之下,有幾次好像也能蒙混過去。
“有人在跟蹤我們吧?!”女人口中一驚一乍,口氣直逼身邊的另一個女玩伴。 “啊!啊!在哪里?”女2托著臉頰,猶如《吶喊》畫像中的小人一般故作驚恐地說道:“親愛的,那是不是我現在該叫救命了呢?” 夜晚似乎并非完全鬼魅,在一種略顯浮夸的演技下,兩個女人用著故意做作的口氣玩著,似乎還玩的蠻開心的。兩人大學本就學的舞臺劇方向,帶著年輕的活性,這樣取鬧也并非如同一般貴美人那般冰涼得毫無生氣。小區的夜色朦朧,還算和諧。唯有一條小小的黑街看上去極不自在,在這條街上,大聲耍鬧也稍微會讓兩人安心一些。 “瞧,就在你身后,就是那個人!”女人突然回頭說道。 女2回頭一看,在街道拐角處看見了一個邋里邋遢的中年人。似乎想要用一種舞臺劇的口吻說道:“啊……原來……原來是他……” 隨后女2向那方向一指,劇本卻意外地跳出了原定的表演方向。 只見街角的那人慌了神,一頭鉆進了小巷,女2本就想用著玩鬧去壯膽,但卻沒想到換來了這樣的恐怖事實,突然間誘發的害怕讓女2慌了神,恍惚間好像還看見了那中年人猙獰的笑容。 隨后女2一怔。 “你沒事吧,蕾蕾。”女人說道。 女人隨即轉頭也向后望去,卻什么也沒有發現。卻感到了莫名的害怕。 自那以后,女2再沒來過這里。
9 老白忙前忙后,跟蹤起來總是很難,雖然自己老是故意掩飾,但是就是總會在某些地方失敗,首先打扮起來也不大會,本來就是個邋遢的人,一時間也沒想過該怎么換個面貌去偽裝自己。所以被小區里人認出來后也挺尷尬。 “一個家里蹲怎么會出來逛了呢?”誰不奇怪。 所以自己跟蹤起來也挺麻煩,在躲過林林總總的其他小區老頭老太以后,就在那一天,他終于還是有機會跟出小區到外面的世界。 為什么說是“外面的世界”,因為老白太久沒出門,沒走多遠竟還迷了路。 小區外的世界也幾經刪改,多少也變了面貌。自己今天一看,竟然才真正體會到自己的確是太久沒有出門了。跟來跟去,總算還是跟到了一所大學面前。那女人進去了,難道說她還沒有畢業?不對,看上去更像是老師。或者就是里面常在的老師,住在校內提供的一些家屬區里面。
老白太久沒出門,對小區以外已經不了解到了一個高度,出來以后,甚至能立馬忘了怎么回去。 此刻也沒想過其他事情,自己出來前也沒有想到過:究竟自己該怎么告訴那女人陷入了危險之中。此刻的他也就只能在校外的一角,呆呆坐在路邊,小賣部里買些碳酸飲料一口一呆地喝了起來。這時候還算能從那種外露式的樓道看見上了幾層。 他想:“在校外坐上一夜,說不定就能知道在哪里出現。” 甚至可能在哪個樓宇間的窗臺上知道她的習慣。望著那些陽臺上那些飄著的內衣內褲,老白也能意味深長地說上一句:“現在的年輕人啊……” 但就在不久以后,其中一個窗內就有人出來收拾了內衣褲,定睛一看,竟然是那個女人,因為穿了睡衣一時間竟然差點看漏。剛才的感慨也隨之而拋到九霄云外去了。 就在一瞬間,一個計劃瞬間在老白腦海里形成。 他想:說不定可以在她家告訴她那些事情! 就這樣單純地想著仿佛自己好像已經能夠找到了答案。于是自己便悄悄混了進去。因為還不算特別晚,所以門衛也能把一個邋遢的中年大叔當作一個老師或者家長來看。要是細看的話就完全經不起考究了。 由于是校內小區的房間,所以管的寬松,在老白那顆正義之心的催促之下,竟然覺得自己大搖大擺地走進學校,去敲一個陌生人的門是一件正常的事情!自己還這樣邋遢竟一點也沒考慮過。夜色迷蒙下,人的智商也變低了嗎? 樓道間踩過輕輕的腳步,然后老白鬼鬼祟祟地上了樓。 一邊害怕著聲音,一邊又被強烈的渴望驅使著。 不久后,深呼吸,敲門。 “誰啊。”
10 “誰啊。” 貓眼中的微光被覆上一只眼睛,老白知道,那是一只美麗的眼睛。偌大的瞳孔時常會在老白的回憶中若影若現。 就在此刻老白渾身一個激靈,口齒不清竟然還結結巴巴起來。一想才發覺到,自己已經不那么習慣說話了。 上次吵架的時候應該已經是三兩天前了吧,一直以來老白都是衣來伸手飯來張口。也已經習慣了這種生活,甚至都已經只能通過吵架才能有多余的說話時間。而在親人們的說三道四之后,他的父母也已經不再管他更多半分,好在老白還并未給二老制造大麻煩,不然妥妥地被趕出家門。 “你是誰啊?”門內傳來悅耳的聲音。 “我……我有重要的事情找你……” 渾身邋遢,胡子沒剃,頭發雜亂無章哪怕還是在夜晚也能感受到強烈的不安。在別人眼中絕非善類。 女人第一時間反應到:乞丐? “請問你有什么事情嗎?” “能不能開開……開門,我想只給你一個人說。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還是有些結巴改不過來。 “你是誰?我為什么要給你開門?”女人開始有些警覺到了什么。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訴你……” “有什么事情不能就在門口說嗎?”那女人道。 “重要的事情……”老白急得話都說不全了。
女人見門外的人急的說不出話了,自己便拉上鏈栓,開了一小個縫隙。而就在此時,門突然就被推撞過來,要不是鏈栓,那人老白早已破門而入。而女人則更是被那一震推倒在地。似乎是他太過焦慮,這樣的突然沖擊下,老白失去了這次說話的機會,女人爬起來后猛烈地朝門撞了過去,直至老白的腿退出門縫后又把門鎖上了。這次是直接反鎖。 “你再不走我要報警了啊!”女人大聲叫道。 老白也為他的魯莽而付出了代價。 女人已經將門前的流浪漢劃為強盜之類。 “喂,是110嗎?”女人大聲在門內叫到:“就大學城里面,有人要搶劫!” 慌忙之中的老白焦慮萬分,不知道該說些什么好。一來什么也傳達到,二來還被這女人看做是一個強盜。 于是在慌忙之中老白快速做了個決定。 “萬龍小區的那個男人,有危險!有危險!”門外的流浪漢深沉地說了好幾遍,從她說話時的偶爾停頓,半是確定了她已經聽過以后。 接著,老白便急急忙忙地跑下樓去了。
11 那個女人也是奇怪,為什么會有一個陌生人來這樣搭訕,并且還說了一些關于那個男人的壞話? 女人本就十分年輕,光滑的皮膚配合十分勻稱的臉蛋。年輕漂亮,于是在一般合理想象之下,大概也演變成一種因為變態嫉妒引發的矛盾,或者說,因為老白毫無理由地突然出現,女人更是將重點放在“有人在跟蹤她,有變態在跟蹤她”這樣的事情上面。于是接下來的幾天,她在日常的生活也變得更為謹慎。 學校更是因為她的報告,調出監控后也反映給校方,門衛更因之而受到處罰。都是些領導卸責的習慣。 然而老白在那之后就很難在對面那棟樓里看見那個女人了。 或者說,那個男人出門在老白眼中變得更加頻繁。也可能是老白的心理作用,本來他白天就不常觀察,突然因為這些事情像是受到了刺激一樣,即使是在白天他也不斷進行著窺視的活動。倘若人沒了交流就會亂想,于是乎就在推測中害怕男人和女人的相見的情況。 會不會是一種約會? 每每想到此處,老白突然就立馬打住,心頭不快。 于是,就在另一個夜晚,便跟蹤了那個男人。
其實在一般時候,男人其實晚上并不常出門,也就是在那一天,突然老白發現了他竟然在晚餐時間就已經開始正常吃飯。當然六七點鐘正常吃飯在一般人眼里肯定是沒有什么破綻,但是這事在老白眼里卻沒那么一般。老白知道,那個男人肯定有什么打算。 不出所料,晚上八點就已正裝經出門。打扮得極為正式,簡直一股成功人士的味道,筆挺的衣裝以及健壯的身材,在夜色中開出一輛黑色轎車。車內燈光昏暗,黃色,里面的面孔被光線襯托得十分曖昧。 老白自然也吸取了上次教訓,至少頭發清理干凈一些,換了身衣服。也因此,上出租車的時候至少沒被立馬趕下車。 “跟上前面的那輛黑色的車。” 司機從后視鏡瞟了一眼邋遢的老白,仿佛明白了什么卻不說破,接著,一踩油門便跟了上去。 不久后,車停到了一個酒吧的門前,男人便走了進去。 老白這副模樣自然不受待見,甚至連門口的臺階都不能坐的程度。只能在遠遠的看著。 大約是三個小時左右,男人領著另一個不認識的女人并且帶回車上。“混蛋。”老白罵道,接著老白也想,這時候,男人該是把那個陌生女人帶回家吧,就這么緊跟著,后半夜肯定就會有事情發生。 陌生的女人,反正和他無關。 然而事情卻出乎意料。 男人并沒有帶著這個女人回家,而是把車開往另一個人跡很少的別墅。
12 司機載著一個邋遢的皮包骨的男人跟著一輛私家車到一處別墅面前,一般人想想也覺得奇怪。一個看上去并不富有的臟兮兮的人竟然跟蹤一輛私家車來到一棟偏遠別墅的面前。究竟會有什么麻煩,司機也多少明白一些。 但這名出租司機卻猶如入世過深的老江湖一樣,什么也沒管就把老白丟在那邊,頭也不回地開著車就走了。這里人煙稀少,實際上也不會有什么出租車會過來。 出租車停在進入園區的拐角處,而那車則是徑直朝向那黑黝黝山間別墅開了進去。 陌生的女人應該是被那男人帶進了別墅。 順著上山的路,不久后就發現私家車就停在那棟別墅面前,而別墅內則光線曖昧,四周似乎很難觀察到里面的動靜。 旁邊依山而建,倘若爬上卻也十分麻煩。但老白知道,若是不快點的話,自己肯定將錯過里面發生的一切。 于是自己也急急忙忙地朝著圍欄處悄悄地翻了過去,順著圍墻往高處爬去。期間還數次跌倒,一次老白那本就油膩的頭還整個栽進泥土地里面。猶如從夜晚生長樹苗,從黑暗中拔出時,臉上還沾滿泥土醒神的清晰草味。而放眼向上看去,盡是黑暗,一些蟲子在他身上亂爬。而且那天下午剛好下過一陣一雨,老白嘴上沒清理干凈泥巴又濕又粘。 “媽的。”老白又罵道,吐了口唾沫。
里面并未察覺到窗戶外的山體上有人,畢竟那時候從那兒望窗外望去也就無非一片黑暗。于是里面的人也沒有任何警覺。 只見男人和女人在喝酒聊天,遠遠望去陌生女人遠白小桌方白桌布前,對男人相視陪笑,伴著一些紅酒。似乎也習慣了這方愉快的味道。當然在這樣對比之下,老白則更是憤憤,巴不得接下來發生什么事情他才開心起來。但是卻又莫名地感到十分緊張。 接著男人起身,朝餐柜走去。 那房間其實布置得也挺奇怪,不過還算合理,吃飯的地方有個鏤空的廚房在內。不遠就能夠到一些廚具,廚房的位置卻稍微有點抬高。仿佛也只能是適合像是屋中男人那般身高的高度才比較方便。 女人也并未回頭,好像也在沉醉在某種曖昧氛圍之中。 他們好像也在說著一些什么話。不過老白就是沒能聽見。 但是老白卻覺得,男人翻弄著櫥柜的樣貌很像是每次夢游時候的狀態,似乎就是在那些整齊排列的餐具中間找著什么樣好用的餐具。難道…… 老白此刻卻被他心中所想驚到。 接著,女人似乎還沉醉在那剛從酒吧出來不久的狀態之中,似乎還是種做白日夢的狀態。也不知道是不是被要求了不要回頭看的“驚喜”還是什么其他的命令。也可能是,在那種女人本身對一棟別墅或是一某種錢權肯定下,乖乖待在座椅上猶如待宰的小鹿。 而此刻,男人摸索到了一把刀。 細看之下就是刀背很厚,如同砍頭斧! 但是那個男人卻并沒有立馬使用。而是在空中比劃幾次,甚至有好幾次都要觸碰到陌生女人的頭頂或是另外的雙肩。然而男人那番動作猶如一個頗具浪漫主義色彩的的獵人,在宰殺生物時候露出一種平靜卻又曖昧的微笑。 就在砍刀還在空中比劃時候,男人似乎是在說什么話,竟然引的那女人咯咯發笑。 甚至那女人還像是聽話一樣地閉上了雙眼。 |